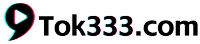责任编辑: annabellestearoom.com
泰晤士河上游的白金汉郡内,有一座名声流传了350年的克利夫顿庄园(Cliveden House)。这座占地375英亩(约1.5平方公里)的乡间园林已归由英国国民信托组织管理,成为对公众开放的郊游之地;昔日达官贵族嬉游与设宴的克利夫顿庄园本身也数度易主,向百姓开放。
旅程初时,从砾石铺成的车道上往克利夫顿大宅开进,岔路上的“爱之泉”十分抢眼:上面丘比特与三位裸女的雕塑固然悦目,当我得知砌造喷泉的大理石是19世纪从意大利搬运过来时,惊诧得倒吸一口气。穷奢极侈如此,原来是当年拥有曼哈顿七成地产物业的大亨威廉•华尔道夫•阿斯特,彼时他将克利夫顿庄园作为新婚礼物,赠送给自己的儿子华尔道夫•阿斯特,而这位第二代阿斯特子爵则特地为新妇南茜•阿斯特送上了“爱之泉”,作为爱之献礼。二战期间,阿斯特家族与英国国民信托组织谈好条件,庄园自此归属于国民信托组织,阿斯特家族仍保留居住权,直到1966年阿斯特最后一位子嗣去世。
 克利夫顿庄园资料图,GettyImages
克利夫顿庄园资料图,GettyImages 阿斯特夫人入主庄园后,家中经常高朋满座,迷倒一众精英阶层。但她的迷人并不止于外貌,后来努力成为了英国国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议员便是一个证明。每次回访纽约,她与同样是美国移居英国的丈夫华尔道夫一度被视为非官方的“英国大使”而处处获得尊重。一战爆发后,华尔道夫命庄园停止娱乐,开始收治战伤的同盟士兵,豪宅变成了一家临时的军事医院。不过,大宅地窖的长廊里英女王慰问护士伤兵的旧照片,证明了此处从未远离过贵族的凝视。
走上庄园大宅前面6英亩的花园绿地,17世纪建造的大露台原封未动,远眺绿地绵延开去的泰晤士低谷。秋高气爽的天底下,开阔视野直达南边的温莎古堡。这座庄园是17世纪时的白金汉郡第二公爵乔治•维利耶为情妇、索尔兹伯里的侯爵夫人而建的宫邸,选址在温莎古堡不远处,据说也是刻意为之。克利夫顿离伦敦车程不到一小时,每逢周末这儿便是游人如鲫。八个风格不同的花园或园林内外,到处是在太阳底下铺开野餐布的人。
克利夫顿豪宅的大堂,一走进来就仿佛置身片场,但你更容易联想到的是中世纪气质幽深十面埋伏的《权力的游戏》,而不是维多利亚时期大家闺秀气派的《唐顿庄园》。除了深色橡木镶板、几幅磅礴的18世纪弗莱芒羊毛与丝绸挂毯之外,最有气势的当属16世纪从一座勃艮第城堡“借用”至今的法国大壁炉。午后时光,坐满了用下午茶餐的人,旧时光的魂魄完全将现实连同阳光挡在了窗帘之外。
对于百姓而言,克利夫顿有时候像个八卦新闻发动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震动全英的“普罗富莫丑闻”就从这里开始:丑闻中的两位主角,一位是当时的陆军大臣与枢密院顾问官、已婚男士约翰•普罗富莫,另一位则是年方19的模特克莉丝汀•基勒。一个夏天的傍晚,两人在克利夫顿庄园的露天泳池边戏水时相识。基勒不久就将这段私情卖给了小报,结果被发现她同时还与一位前苏联间谍有染,一件道德八卦当即上升成为国家安全事件。这场丑闻事件直接打击了保守党政府,并使之在一年后垮台。
三十年前曾有电影人以此为题材拍过影片《丑闻》,而迎来送往过无数达官贵人的克利夫顿庄园,也不讳丑闻的点缀。毕竟,1666年克利夫顿的建造就来自白金汉第二公爵与索尔兹伯里侯爵夫人的“不道德关系”。不仅如此,当年这位公爵还公然对侯爵夫人的丈夫发起决斗邀请,据说“看到丈夫遭受致命伤,侯爵夫人丝毫不为所动。”
普罗富莫与基勒第一次见面的户外泳池今天还在。一旁挨着19世纪时加建的30米高水塔,当年的建筑设计师亨利•克拉顿显然觉得光是“水塔”的外貌华丽不足,于是将塔楼修成了金灿灿的钟楼,每隔一刻钟敲响一次,直到今天。18、19世纪遭遇过两次大火后,克利夫顿的重建由英国议会大厦与“大笨钟”的建筑设计师查尔斯•巴里操刀,泳池边上的这幢钟楼,也因此像极了迷你版的大笨钟。
 克利夫顿庄园钟楼的重建工作,由设计伦敦“大笨钟”的建筑师查尔斯•巴里负责。一旁的露天泳池,便是1960年代“普罗富莫丑闻”事件的起源地。
克利夫顿庄园钟楼的重建工作,由设计伦敦“大笨钟”的建筑师查尔斯•巴里负责。一旁的露天泳池,便是1960年代“普罗富莫丑闻”事件的起源地。 走到池边刚想跳下水,忽然发现水面上悠哉游哉漂荡着一大一小两只鸭子。盯着小鸭子欢快又笨拙的泳姿,我想起了流传极广的童书《柳林风声》,书里的鼹鼠、河鼠、蟾蜍与獾在乡间、河畔的历险记。事实上,这本书的作者肯尼思•格雷厄姆还真是在克利夫顿河段泛舟时,获得了写小动物们的故事灵感。
初时,格雷厄姆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是为了给小儿子阿拉斯泰尔当睡前故事讲的。尽管当成书后的《柳林风声》在1908年出版时并未得到评论界多少反响,但迄今已在全球卖了几百万本的成绩,证明了这本小书的生命力。河鼠与鼹鼠在河上泛舟的插画,成为好几代英国人的童年回忆,由画家E.H.谢泼德创作的这幅插画已被收藏到了大英图书馆里。格雷厄姆与他笔下在绿水上泛舟的克利夫顿河岸上,还伫立着一幢“春舍”,当年阿斯特家族为了克利夫顿常客维多利亚女王专门建起来的舒适农舍,今天谁来都能租住下。
 “春舍”(Spring Cottage)资料图片,GettyImages
“春舍”(Spring Cottage)资料图片,GettyImages 仔细看,克利夫顿大宅里收藏了不少中国家具与装饰物。从大堂走上楼梯时,赫然出现一座桃花心木铜锣,从前入门处放着五片乌木屏风,镀金图案描绘的是古代中国的生活图景,但朝代不详。在17世纪留下来的一间伯爵使用的书房内,窗台上放着两个白瓷大花瓶,瓶身刻有“朱子治家格言”。这一切都令我联想到明清时代西方曾刮起过的“中国热”。如果到外面的几个花园里散步,你会发现其中一个花园里立着一座19世纪建的“中国宝塔”。凑近细看塔上亦中亦西的构造与设计,我感觉这更接近当年西方对东方想像之下的产物。
到了1893年,当听说庄园要卖给美国人时,维多利亚女王十分不悦,但这并没有阻挡克利夫顿当代史的华丽揭幕。据说老华尔道夫有社交恐惧症,他接手克利夫顿以后,并没有像几家前任主人那样豪迈设宴夜夜笙歌,而是将千金掷于室内装饰之上:比如从巴黎近郊的埃涅尔城堡里,将一间房内所有路易十五时期风格的原木镶板与装饰原封不动拆搬过来,结果就是我们眼前的这间“法兰西用餐大厅”。
三年前,在德国出生、英格兰长大的Chris Hannon接任了餐厅的行政总厨。从小耳闻当厨师的祖父在港口迎送各国各地客人的故事,他对学厨也逐渐生出兴趣。Chris学理科出身,他对我说,做菜有点像做化学实验,他经常自己试用各种食材做搭配,看看各种配料之间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我们的餐盘上就有一些不寻常的搭配,比如比目鱼配上苹果泥、用红酒海鲈鱼、鱼饼酿朝鲜蓟,甚至用上荔枝混搭白巧克力与开心果做成甜点。在一座看似城府极深的庄园里工作,Chris却告知他乐意让餐厅气氛变得更随意一些,客人的衣着和礼节都可以不太拘束。
 Cliveden House行政总厨Chris Hannon
Cliveden House行政总厨Chris Hannon Chris虽是学法厨的底子,十分重视酱汁的调制,但他提及,过去几年里,厨师们喜欢往一道菜里塞上复杂多样的食材,这种做法如今已被简化食材、一种食材多种吃法的风尚所取代。酱汁讲究,但即使是冬季松露烩米饭,口感虽浓郁却并不厚重,烤鹌鹑就配了一点甜玉米、干葱和松子酱。上面已提到过的一道比目鱼,用了大头菜做汁,浇到铺鱼面的海篷子之上,配菜味道点到即止,保留主食材的鲜味为重。
与任何有追求的厨师一样,Chris尽量用新鲜的本地食材。然而由于庄园的公共区域归国民信托组织管理,厨师并没有自己的蔬菜园。庄园内的蔬菜地里倒是什么菜都有,Chris告知,他曾提出向“国民信托”购买这地里的菜,然而对方没同意。我去蔬菜地里逛了逛,看到大部分夏季成熟的豆角、西红柿都要熟烂了,心想这实在可惜。
 1926年,萧伯纳到访克利夫顿庄园
1926年,萧伯纳到访克利夫顿庄园 夕阳从八面来风的巴洛克门窗透进来,西服笔挺的侍应生正一丝不苟地量度“法兰西用餐大厅”长桌上的纯白色桌布是不是左右对称。曾落座在这张长桌旁的,曾有甘地、萧伯纳与丘吉尔。丘吉尔做客时,他与庄园女主人南茜•阿斯特对着坐。两人的交往曾留下不少互怂对白,其中一段在英国广为流传的丘吉尔对阿斯特夫人的经典损语是这样的:“你可真是丑啊。反正明儿我就会酒醒,而你呢,还是会那么丑。”
而事实上,不论是克利夫顿大宅里的巨幅画像、或是史上留下来的阿斯特夫人照片,放在大众审美标准下审视,她的外表都恰恰与“丑陋”相反。至于她与丘吉尔之间的“互辱”,有旁人则解读为“绕圈子的互表衷肠”。
文章编辑: annabellestearoom.com